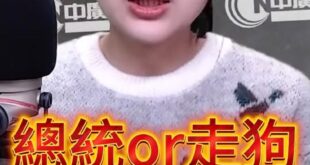〈還若彤公道者,必翠蓮矣〉
網友傳來陳翠蓮老師的最新臉文,是對於「公民醒不醒」所撰文章的反駁。大致的意思是,陳翠蓮老師認為「公民醒不醒」的文章只是為了駁斥陳翠蓮等人的研究成果而寫,雖然引出了史料為根據,但並沒有反駁自己和許雪姬研究所引用的主要證據,且並未提出對於忠義服務隊有什麼具體看法,因此只是為否認而否認,目的只是讓二二八事件處於各說各話的狀態,不是為了追究真相。
我是邊看邊笑,這件事如果我來講,肯定又要被貼標籤,但出於陳翠蓮之口,大家應該沒有話說了吧。
多少人批評我「輕信政府檔案」,說「政府檔案不可信」,現在好了,陳翠蓮教授自己也揭露了,她自己對於忠義服務隊的研究成果,所根據的「主要證據」、「核心檔案證據」,一共是三種:
1.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〈二二八事變之真像〉、〈事變十日記〉
2.國家安全局所藏的許德輝〈台灣二二八事變反間工作報告〉
3.警備總部的〈台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〉
三個核心證據中,倒有兩個是政府檔案(剩下的一個則是「軍情高層或主要當事者」柯遠芬自己私人的說法)。
陳翠蓮教授特別指出,警備總部的〈台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〉更清楚說明:
「軍統林頂立如何透過他召集黑道流氓組織忠義服務隊,滲透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、從事「反間」工作,並且「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花蓮各地亦有如法進行,收效宏大」」
有趣的點是,陳翠蓮切掉了原文「收效宏大」後面的文字,其實加上後面的文字、去看全文,〈台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〉中,警備總部的意思反而是要說,這個反間工作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⋯⋯。
陳翠蓮的引文:
「乃派許德輝同志出面掌握台北廿二角落流氓首領及一部分純良學生,指示方針,參加為反間工作,出為鎮壓暴徒並勸導市民,勿為利用。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花蓮各地亦有如法進行,收效宏大」
實際上的全文:
「乃派許德輝同志出面掌握台北廿二角落流氓首領及一部分純良學生,指示方針,參加為反間工作,出為鎮壓暴徒並勸導市民,勿為利用。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花蓮各地亦有如法進行,收效宏大,唯吾人在台工作建立不久,人員稀少,致不能發動全面工作達成任務,殊為遺憾。」
這種掐頭或去尾就足以改變史料意義的事情,其實非常多,我在我的新書《如是228》中也提到了一個例子,同樣出自陳翠蓮教授、同樣截去史料尾巴而改變史料意義。
既然陳老師覺得「似乎應該加以回應了」,或許也可以回應一下我在《如是228》中提出的疑惑。
以下節錄自拙著《如是228》:
–
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,同一本《台灣二月革命》,其實對同一個事件,存在兩種不同的、邏輯上互斥的說法,即到底是楊亮功「先登岸」才下令殺戮,還是「先下令殺戮」楊亮功才登岸。兩個自我矛盾的說法,前後僅數頁之隔。
–
(按:三月)八日下午三時許,閩台監察使在憲兵第四團兩營保衛之下,到達基隆,即下令要塞司令部與憲兵夾攻市民,於是「市街戰」勃發,大砲、機槍、步槍齊响,殺死許許多多的市民,老幼男婦都有,直到晚上十時,抗戰民眾被殺光了,楊始登岸,分乘軍用卡車,直駛台北,但途中又遭民眾襲擊,傷隨員衛士各一名。(第十八頁)
–
無獨有偶地,後面這一種《台灣二月革命》(第十八頁)的說法,也為學者陳翠蓮在《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》第三百六十頁中整段加以引用,用來證明三月八日下午發生的「鎮壓行動」,但她似乎有意略去了段末最後兩句「但途中又遭民眾襲擊,傷隨員衛士各一名」。大家可以感覺到,引、不引,觀感上差很多。引了,看起來是雙方互有斬獲;不引,看起來是軍隊藉優勢殺戮,即鎮壓。當然,也有另一種可能,就是她不採信「民眾襲擊」的說法,而認為這是軍方自己放槍製造事端。但無論如何,原文不是這樣講的。沒有隻字片語的說明,證據想剪裁就裁掉了。
最讓人困惑的並不止於此,《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》引用《臺灣二月革命》來說明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下午的鎮壓存在,但它同時也全文照引了何聘儒〈蔣軍鎮壓臺灣人民紀實〉的說法,來證明三月九日的鎮壓行動也存在。
–
(三月九日午前)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,尚未靠岸時,即遭岸上的群眾怒吼反抗。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,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,多人被打得頭破腳斷,肝腸滿地,甚至孕婦、小孩亦不倖免。甚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,碼頭附近一帶,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。
–
這就造就了一個荒謬的結論,一批勇敢的基隆人,前一天(三月八日)才被大砲、機槍、步槍,從下午三點殺到晚上十點才殺光,隔天(三月九日)一早,居然又有一批勇敢的基隆人(還包含孕婦小孩)不怕死,特地跑去幾個小時前才發生大屠殺(屍體恐怕還沒時間移開)的港邊送死?
#如是二二八好評發售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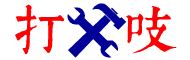 黑特民進黨 The night is darkest just before the dawn.
黑特民進黨 The night is darkest just before the dawn.